萨斯认为,整个美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成年危机。美国的年轻人似乎永远停留在了青少年阶段,他们不懂得做一个成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该如何扮演好成年人的角色。很多人甚至认为,没必要为此付出努力。
在英语中,“Adult”
(成年人)
曾经是个意义明确的名词,但在过去几年,它在社交媒体中却更多被当成了动词使用,在推特等平台出现了一个新的话题标签:“#做一个成年人”
(#adulting)
,年轻人借此来表达自己“被迫成年”的无奈:“午夜洗衣/洗碗/打扫浴室#做一个成年人”,“按时支付本月账单#做一个成年人”,“既然不能一连8小时上网刷剧,那就出门买菜#做一个成年人”……
2016年,美国语言学会提名“adulting”为英语语言中最具创意的构词,可见其热门程度。
对那些不喜欢听到将“adult”名词动用的人——也就是真正的成年人——来说,“adulting”一词充满讽刺意味,因为它只是用来描述交税或“忙于各种家务”等成年人本该承担的事务,这是成年人的责任所在。但是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说,做一个成年人是一种可能被视为笑话的角色扮演。
曾任美国米德兰大学校长的本·萨斯
(Ben Sasse)
对这种情况感到了担忧。在他看来,以往任何时候,“成年”一词都含义明确。告别青少年时代,做一个成年人,在概念上是清晰的,它是上一代人赠予年轻人的大礼,但今天这样的认识已不多见。他把当今美国年轻人称为“迟迟长不大的一代”,甚至“巨婴”的一代,他们造出新词,嘲讽老一辈过去的理想——希望成为负责任、勇于担当的人。

本·萨斯(Ben Sasse),现为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参议院,2010-2014年担任美国米德兰大学校长。
萨斯认为,整个美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成年危机。美国的年轻人似乎永远停留在了青少年阶段,他们不懂得做一个成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该如何扮演好成年人的角色。很多人甚至认为,没必要为此付出努力。
原文作者 | 本·萨斯
摘编 | 肖舒妍
青春期的意义
温蒂 :你又怯懦又缺心眼儿!
彼得 :我怎么缺心眼儿?
温蒂 :你没长大,你还是个孩子。
— 詹姆斯·马修·巴里《彼得·潘》
《彼得·潘》讲述了一个拒绝长大的小男孩的故事,读者常误以为这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童话故事,事实却远非如此。作者巴里笔下的经典人物彼得并不是一个值得赞美的英雄人物,他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彼得说 :“我不想去学校学习那些严肃的东西,我不想长大。”
最后,他甚至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从中获取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故事结尾处,温蒂努力唤起彼得的记忆 :
温蒂说起他们的死敌霍克船长的时候,彼得饶有兴趣地问 :“谁是霍克船长?”
温蒂惊呆了 :“你不记得了吗?你杀了他,救了我们所有人!”
“杀了他们以后,我就全忘了。”彼得漫不经心地回答。
彼得·潘拒绝成长,但那些迷失的少年却在一天天地长大,温蒂也是。温蒂有个女儿叫简,偶尔也去梦幻岛,但最后逃离了那里,简的女儿玛格丽特也像妈妈一样,不愿被困在梦幻岛,所以选择了离开,故事就这样一直继续着。每个人都在前进,除了彼得·潘。他从未改变,从未长大。

《拒绝成年》,[美] 本·萨斯著,贾文娟译,新民说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
只活在当下,活在此刻,并不是一种自由,甚至也并不符合人性。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我们记得过去,理解人之本性,并努力发展自我。我们有理想,有抱负,也会不断展望未来。
没有哪个文明能够接纳无尽的青年期。历史上一些尊贵骄奢的家族曾试图接纳它,但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很少有好的结果。很多文化中其实并不存在一个青年期,即使有,人们也会通过某种集体仪式,迫使其成员早日脱离这一阶段。
传统上,成年的路径很清晰,儿童经过一定的顺序长大成人,但并不是经过一个个的日期,而是经历一系列的事件,取得一定的成绩。古罗马法律条文中将成年前明确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7年——婴孩期
(从出生到6岁)
、童年期
(7岁到13岁)
、青年期
(14岁到20岁)
。这种“三阶段”的基本划分一直沿用至今。第一个阶段孩子对父母,特别是对母亲高度依赖,他们从母亲那里得到食物、关爱和安全感。当孩子们能离开母亲几个小时,也就是非常短暂地初尝到独立滋味的时候,这一阶段也便走入尾声。这个时候,孩子们会发现,离开母亲六七个,甚至十个小时,也不会对自己有任何不良影响。
第二个阶段,孩子渐渐进入青春期,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他们在饮食、服装方面有了更多选择,自我约束力增强。五百多年前,廉价出版物大量涌现,孩子们开始学习阅读,运用逻辑推理,理解一些更复杂的概念,如因果关系、短期投入与长期收益等;日渐成熟的孩子不再仅仅着眼于眼前。
第三个阶段是青年期,它是连接“童年期”和“成人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英文里的adolescence
(青年期)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意思是“长大”,大约15世纪时开始成为广泛使用的词,指在生理、情绪、经济、性格等方面接近完全成熟。儿童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
20世纪50年代将“青年期”称作“暂停的成人期”,他认为,这个阶段个体会停下来不断尝试或试验,逐渐确立自己的身份,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责任开始被理解为一种个体欣然接受的东西,而非机械忍受的负担。青年期也是成长过程中的温室期,这一时期,大孩子在即将成年的最后阶段仍可以得到保护;宽容和鼓励青年期表明,在父母和其他权威人士看来,让儿童通过一段时期的准备以后再最终永久性地离巢,至关重要。
一些社会会有明确的仪式,见证一个孩子告别童年,进入成人期。这些仪式的目的是要青少年对下一个人生阶段的任务有清醒的认识,提醒他们应摆脱儿童期的依赖心理,学会独立,勇于承担责任。犹太人和拉丁美洲的家长会给孩子举行成人礼,古代斯巴达人是较为极端的例子,导演扎克·施耐德
(Zack Snyder)
2006年执导的动作电影《斯巴达300勇士》中有生动的刻画。斯巴达男孩 7 岁开始就要进入军事学校,12 岁时便来到荒野中锻炼,除了一件红色的斗篷,身上没有任何装备。斯巴达人希望他们年轻的士兵能自食其力,填饱肚子,证明自己具备基本生存能力,偷盗当然是禁止的。生活在巴西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的萨特玛维部落,会让 13 岁的男孩戴上装满“子弹蚁”的手套,这种体型很大的蚂蚁咬起人来和被子弹射中一样疼痛难忍。孩子们通过忍受剧痛来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
《斯巴达300勇士》剧照。
“成人礼”标志着一个人从一个群体进入了另一个群体,这往往值得庆祝,因为它意味着被部落、军团、宗教组织或一个民族正式接纳。成人礼或神圣或世俗,但其目的是一致的。虽然各种成人礼都会让孩子们经历艰辛,但其初衷并不是要他们当众出丑,或狼狈不堪,而是帮孩子认识到成年期要经历的挫折与坎坷,以及离家独立生活后,为谋生存,必须要付出的劳动与坚韧。从各种成人礼也可以看出,普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完全独立前,能切身体会生活的不易和生存所需的必要品质。孩子们需要这样目标明确的仪式,可惜今天这种观念已经越来越淡薄,因此也带来越发严峻的社会问题。
美国也有成人礼。只是相比其他文化以达到某种结果或取得某种成绩为目标的成人礼,我们的成人仪式似乎缺少了明确的指向。美国人的成人礼并不复杂,如舞会前拍照 ;等上一位同学下台后,控制好时间上台领取高中毕业证——当然,几乎每一个没有辍学的孩子都能拿得到。
电影《歌舞青春》剧照。
美国仍有一些团体会迫使他们的成员直面艰险,例如海军陆战队和海豹突击队都会让年轻队员经历地狱般的苦练,才最终接纳他们为完全合格的队员。拒绝现代文明的阿米什人有着“游历”的传统,长辈们会允许年轻人离开家,去外面体验一段时间,与其他文化的人交往,穿阿米什人从来不穿的鲜艳衣服,也可以开车、饮酒,甚至使用一些违禁物品,之后才让年轻人做出选择 :是否愿意回归阿米什社区。这个时候,年轻人就要经过思考,做出出于本意的主动选择,确定自己是否要成为一名阿米什成年人。
当然,很多外在因素也会影响青年期的长短。出生在家境窘迫或父母早亡家庭的孩子通常较为早熟,他们会更自然地过渡到成年期;饱受战乱之苦的民族通常也没有延长青年期的时间和空间,想想看,如果 1994 年你是一名生活在波斯尼亚或卢旺达的 13 岁少年,父亲或母亲,或双亲都已经被杀害,那就只能选择快速成年,否则就要遭遇和父母同样的下场。
青年期与婴孩期、童年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终点和持续时间并没有那么明确。青年期可能并不存在,或持续时间较短,但也可能较长。没有经历青年期是一种遗憾;如果有意为之,短暂的青年期也并无不妥;如果目标明确,持续时间较长的青年期也未尝不可,例如:一些学徒往往要跟师傅学习多年,才能掌握一门手艺,也有一些年轻人,要长期浸淫于另一种文化,才能完全掌握一门外语。
但永久性青年期就另当别论了。
青年期是手段,不是目的,帮助孩子向成年期顺利过渡才是其存在的真正意义。斯巴达人让他们年轻的士兵经历痛苦折磨,并不是因为痛苦本身值得赞颂,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肩负保家卫国重任的公民具备尽职尽责的知识、能力、坚韧和意识。青年期有着鲜明的目标,它不应该无限期或永久性地存在。
美国的情形有所不同。青年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美国人很难众口一词。为什么一个生理上成年的孩子,迟迟不能肩负起他本该肩负的责任,而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却能袖手旁观?美国人没有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达成共识。孩子们也能察觉到这种大的文化趋势,并以各种消磨时光的方式做以回应。但如果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时间,又为什么要消磨它?要知道,老一辈美国人曾想方设法“赎回时间”。
电影《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剧照。
永久性青年期的出现
为什么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在他们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却如此被动颓废,成年后依然愿意蜗居于父母的地下室,离不开刷剧点餐的手机?三言两语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要充分理解这一问题,就要简要回顾二战结束后的前几十年里美国社会的五大变化。
第一,虽然 2008 年经济衰退的阴影依然笼罩美国,就业情况长期不稳并可能持续恶化,但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和世界其他国家,我们仍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显然,这是好消息 — 但同时也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过去70年积累的惊人的物质财富使美国的青少年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更沉迷于享乐。
第二,因为过度消费这一不良习惯,我们的孩子已经不懂得何为“生产”。他们的成长环境中很少有劳动和工作的影子,今天的孩子很可能会将“劳动”等同于一份工作,而且也不大可能和以前的孩子一样,继续从事父母的工作,如留在家庭农场或牧场。正因如此,孩子们很难切身感受到父辈工作的艰辛,也无法像曾祖辈一样从父母那里继承对劳动的忠诚和热爱。如今,大多数孩子并不与其他年龄段的人交往,填补这种成年权威真空和劳作空缺的,是学校的同伴文化和近年来出现的数字世界颇为自恋的自主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几十年前的年轻人,尽管今天的孩子待在父母家中的时间越来越久,却越来越早地脱离了长辈的社交圈和优良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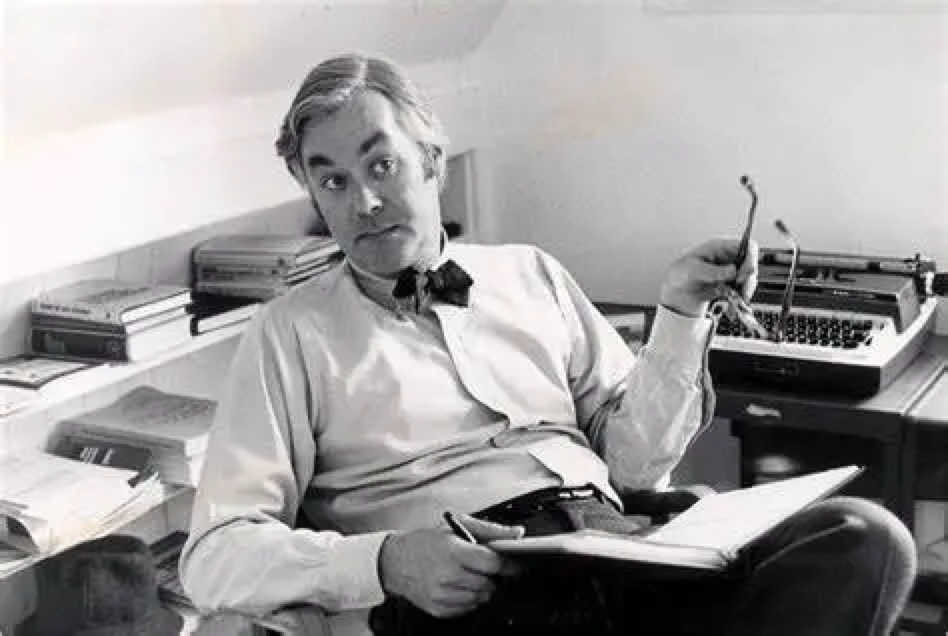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美国社会学家,美国民主党人士,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第三,半个世纪以来有人发出的“核心家庭岌岌可危”的警示似乎已成现实。家庭生活的断裂使很多孩子失去了顺利过渡到独立成年生活的可靠环境。著名社会学家、民主党人莫伊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最早敲响了“黑人家庭生活可能解体”的警钟,1965 年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莫伊尼汉报告指出,联邦官员应该为家庭的瓦解感到恐慌。当时非裔美国人的非婚生子女出生率高达 25%,而白人群体的这一比例远不到 10%。50 年后我们发现,它无关种族,因为这一问题已相当普遍。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
(Charles Murray)
、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Putnam)
、作家J. D. 万斯
(J. D. Vance)
在他们的著作里也都指出,这一可悲的变化并不仅限于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今天白人的非婚生子女出生率飙升到了 30%,比 20 世纪 60 年代黑人群体的这一比例还要高。尽管未成年人的怀孕人数有所下降,但城市研究所发布的《莫伊尼汉报告再回顾》却显示:非婚生黑人婴儿的出生率已超 70%。

《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Bell Curve),Richard J. Her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著。
第四,人们认为必须为青少年提供中等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已经忘记,历史上,学校教育并不是一个人长大成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一个世纪以前,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认识。20世纪初,在美国大多数州,家长和学生可以选择是否一整年都在中学校园度过,短短30年后,中学教育成为每个学生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中学教育固然有其价值与意义,但意想不到的是,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让孩子们失去了顺利成年所必备的劳动环境和与长辈等其他年龄段的人们共处的机会。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家庭的餐桌边仍然有老年人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孩子们,成长不仅仅只是学习成绩的提升。
令人不解的是,就在学校教育占据了我们对教育的所有想象的时候,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的教育却越来越肤浅。自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规定不得在校内祈祷,以及公立学校禁止开设宗教课程以来,学校教育更加世俗化,制度化。无论你是否赞同这一决定,毋庸置疑,它使孩子们越来越远离存在问题,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问题。
中等教育不再能帮助学生在离开校园后谋得稳定理想的职业,这也是学校德育教育缺失的原因之一。此前中等教育是顺利求职的保障,教育史学家保拉·法斯
(Paula Fass)
探寻了为何学校教育越来越趋向“批量生产”,而无视其重要培养目的——促进青少年成长为积极进取的成年人。“对于即将进入大学校园的高中生来说,高中阶段只是其青少年时期的一个中转站,除了更多课程选择外,高中并没有为孩子们提供其他更有意义的活动……”当高中文凭不再是全职工作或中产阶级的保障,也无法满足我们对成年人的各种预期时,高中教育就难免为人所诟病。同伴文化,或者说同辈文化,开始填补学校意义缺席的真空,孩子们不再视教师为行为楷模,教师也不再认为传递从经历和经验中积淀的智慧,提升学生品德修养是其应尽之责。于是,孩子们放眼四顾,周围的同学和同龄人成为能够效仿或参照的唯一对象。
第五,20 世纪 60 年代是一个充满抗议和危机的时代,多种冲突矛头直指同一个问题 :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国的自我管理试验是否独一无二。形形色色的抵抗活动,特别是民权运动,促使美国最终践行了《独立宣言》中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几百年后,我们终于实现了“不论男女、种族,人人平等”。还有一些争论,如某些战争是否不义,滥用药物的成本,划分性别界限是否有意义等,也都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后来慢慢沉寂了,这并不是说,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恰恰相反,我们似乎决定不下结论,不达成和解,这也正是最可悲的地方。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一些文化上的争议,我们没有理性的思考,没有开展广泛的讨论,达成新的共识,而是任由极端化占据上风。正因为我们的被动不作为,流行文化和庸俗浅薄才乘虚而入,逐渐取代传统,这已成为当今美国人的共同感受。
曾将这个多元化的国家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目标和共同理想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继续崩塌。回首那段动荡不堪的岁月,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所未有的消费至上主义,日益稀少的劳动机会和数目惊人的家庭的破碎使美国青少年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美国人的生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原文作者 | [美] 本·萨斯
摘编 | 肖舒妍
编辑 | 李永博;王青
校对 | 陈荻雁
最新评论